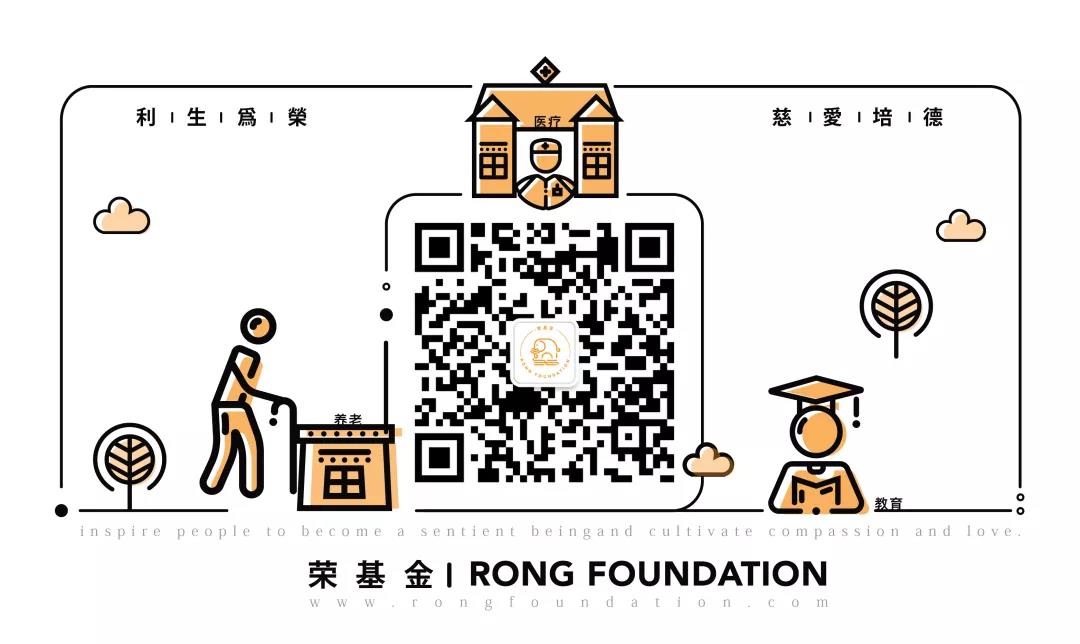一朵玫瑰,
即使它带刺也是生命。
早上它是鲜艳的,是生命;
晚上就枯萎了,也是生命。
爱是如你所是,而非如我所愿。
民众护理院里有位风趣幽默的“马局长”,很多参加老者不孤活动的志愿者都争先恐后的要来探望这位83岁的老人家。今天是我初见“马局长”,进房门时他正在洗手间里自己洗衣服,他说自己还会做衣服呢,年轻时曾是天安门更换路灯的无名英雄,可谓“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模范好男人。
“马局长”非常健谈,是一位生长在牛街的老北京人,他的歇后语一句接一句,总是可以逗乐在场的每一个人:“哎,又摔了一跤,每次都是摔过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左脚是不能踩在右脚上的!可下次啊,外甥打灯,照‘舅’!”好心态的“马局长”还会自嘲说:“我现在特别想得开,没什么好较真和生气的,有气呀?放两个屁不就好了!”
除了腿脚行动不便,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何疾病需要在这里被照顾和护理。和摆在床头照片对比看来,也根本看不出已是83岁高龄,甚至比起当年反而更显和蔼、富态,后来我得知“马局长”患的病是阿尔兹海默症,于是回忆起他的确会说一些重复的话,包括已经不能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控制而导致摔跤。
不是每一位老人都可以康复
和“马局长”的“会晤”让我想起第一次来民众护理院做志愿者时遇到的那位中风后正在康复的钱爷爷,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治疗的话题。
他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摔倒了,希望自己可以尽快恢复如常,这样可以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在这儿恢复其实除了药物治疗和康健恢复,更重要的是心态,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有家人探望,以及志愿者来陪伴,哪怕只是聊聊天也很快乐。”所以钱爷爷认为,药疗不如心疗,心疗不如话疗。
不是每一位脑中风患者都可以恢复如常,我在松堂关怀医院陪伴的另一位老人——刘老师,由于中风已经丧失身体左侧肢体的所有运动能力,甚至要经常擦口水。我曾经在《身体从未忘记》这本书中了解到,中风会对大脑造成物理创伤,尤其是负责语言的布洛卡区是不能工作的,所以患者不能把感受和想法转换成语言表达出来。我和另外两位志愿者在陪伴刘老师的时候,就遇到了沟通的障碍。
刘老师只能说单字,或者点头、摇头,如果表达长句字时就只能用“咻咻咻”来代替,同时右手会放在嘴前,再向远处滑动。似乎这个动作可以利于他的表达,而不同声调的“咻咻咻”可以利于我们理解他的意思一般。我和另外两位志愿者连猜带蒙的和他“畅谈”了半小时。作为一位数学老师,曾经在讲台上手执教鞭,对着台下的学生高谈阔论,传授毕生所学的知识,而今坐在轮椅上连简单的对话都很难,这两种画面的对比,令人唏嘘不已。
不是每一位老人都可以选择
不是每一位老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离开的方式。
今年9月份我在松堂关怀医院陪伴的张爷爷给我的冲击和反思很多。那天我站在门口,看到他睁大双眼热切的望着我,于是我决定走过去陪伴他。其实他是我陪伴的第一位男性老人,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我并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老爷爷,所以我从参与老人陪伴活动开始就一直尽量选择老奶奶为服务对象。
当我走近张爷爷时才发现,他双手被绑在床上,手上扎着吊针,手背上死皮很多,牙齿基本掉光了,身旁戴着尿袋。此前接受志愿者培训时曾了解到,束缚带是为了防止老人抓挠身体或弄掉医疗辅助设施。经过自我介绍和简单的开场白之后,我发现张爷爷并不能意识清醒的与我互动。他总是望着我,不停抿着嘴,没有牙齿也不利于他吐字,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们就这样陷入了尴尬。
张爷爷开始不断望向我身后的窗外发呆,一会又踢踹被子,在床上扭来扭去,很不舒服的样子。当我伸出手,试图握住他时,他把手抽走了。那个瞬间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不清醒的老人,在不能“话疗”陪伴也不能做抚触陪伴的时候,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的安静,让我们听到了隔壁床老人收音机里播放出的音乐。就这样,我们听着音乐,我望着他的眼睛,一直静静的坐着。他凝视了我一会,眼神又飘走了,继续在床上不安宁的扭动着。于是我决定给他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向他介绍我的工作,家庭,爱好,出生地等等,时而还帮他拉扯一下被子,为他盖好。慢慢的,张爷爷睡着了。我像是给一个孩子讲了睡前故事一样,让他安静的熟睡了。
一朵玫瑰,即使它带刺也是生命,早上它是鲜艳的,是生命;晚上枯萎了,也是生命。
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停留
看着病床上的张爷爷,在某一瞬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个聪明、热情、重情义的白羊座,在他离世前曾和我妈提到过,将来不要墓地,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游山玩水,去到还没来得及去过的地方。父亲的离开是非常突然的变故,我曾一直处在懊悔和自责之中。
现在看到被束缚带绑在床上无法安宁又不能表达的张爷爷,让我想到父亲离开时其实是没有受任何的病痛与折磨的,这对于好动又害怕打针的父亲来说,或许是最轻松的离开方式。尽管我有一万个不舍得,但这是他“选择“的方式。此情此景让我领悟到那句:“爱是如其所是,而非如我所愿。”
在父亲离世一周年之际,我和妈妈去骨灰堂看望他,出来时我问妈妈:“以后有何打算,是否想过和父亲合葬在一起?”我们步行在人民公墓的坡道上,妈妈牵着我的手说:“活着的时候对我好点,死了随便扔,跟你爸一样,撒大海吧。墓地就不必了,你们去看那个小盒子有什么用,又能去几次呢?为这种形式的东西还花这么多钱,没必要。”中国人一直避讳谈论死亡话题,妈妈的回答让我挺意外,原来他们对自己身后事早就有了预期计划,而且并非我们子女想象的那么传统,相反,开放度很高。
就像妈妈说的,人生中有太多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抑或有很多不得不做的事,在牵扯着我们的精力。只有专注当下,为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积极负责,对每一个生命全然的接纳,才是更加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今后要一直做的事。痛苦的另一面是快乐,恐惧的另一面是自由,用我的积极、负责任、勇敢和爱,为身边的人创造一个真诚、温暖、和平、喜悦的世界。
撰稿人/肥冷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