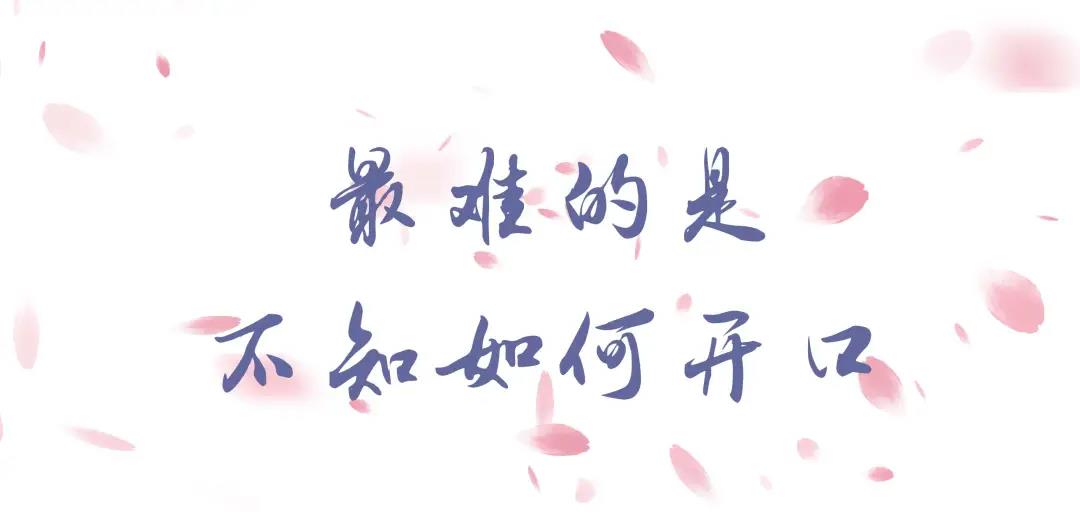那天我一个人在家,在厨房里做晚餐。用各种蔬菜、蘑菇、豆腐等煮成了一小锅颜色与营养俱丰富的热腾腾的面条。我在心里对妈妈说,你看,妈妈,我有好好吃饭哦。虽然,妈妈已经离开快七年了。
我向来对吃饭这件事很不在意,一直成了妈妈生前的心病。有一次我好好的做了一顿饭,拍照发给妈妈,妈妈非常欣喜,说太好了,以后就这样好好吃饭!所以妈妈走后,每当我认真做饭时,都会想着和天上的妈妈说一声,你看,我有听你的话,我是乖女儿。
查出癌症之前,妈妈身体一直很好,除了膝盖有一些退行性病变,她一直是我心目中长寿老人的样子。有一天我堵车无聊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她锻炼刚回来,她说要活到120岁,让我80岁还能有个妈妈,而且要健康,不给我们添麻烦。漫漫车海中,我幸福的想哭。
那个夏天其实还是有些征兆的。妈妈的肚子疼的很厉害,被诊断为肾结石。感觉没那么难受了,妈妈就去美国探望妹妹了。在美国时腹部依然疼痛,而且每到傍晚站都站不住。因为美国看病实在太难了,妈妈又是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那一类人。她选择谁也没告诉,就那样忍着,大家都没有看出她的丝毫不适。
两个月过后回国第二天去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是输尿管癌三期了。还记得妈妈给我打电话时用平静的语气诉说,而我已是五雷轰顶。当天晚上妈妈就草拟了遗书。妈妈幼年丧母,生活艰辛,13岁才上小学,读大学期间正逢文革,任学生会主席的她遭受迫害,毕业后支持大西北宁夏建设。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就讲述的是宁夏的故事,妈妈是向宁夏奉献了青春和一生的老一代建设者。这些经历使得妈妈有一种大丈夫般的豪爽洒脱。
彼时我从悲伤中振作起来,觉得妈妈还远没有到这一步。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妈妈的癌症也不是那样的致命,肯定有办法的。妈妈也于确诊后的第二天便来到北京,开始了治疗。那时候全家人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打败癌症。
先是做了手术,住院前的一晚,我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记忆中很久没有和妈妈这样亲密的躺在一起。虽然我们彼此深爱对方,但好像我们这两个时代长大的人都不擅于表达。我一夜无眠,拉着妈妈瘦小柔软的手,心里充满了要失去妈妈的恐惧,默默哭了一晚。
手术过程中发现妈妈一侧肾已经坏死,周围部分淋巴有癌细胞浸润。医生说手术挺成功,做的应该挺干净。住院的时候我每天陪伴妈妈,医院不允许陪床,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探视时间。中午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在外面流浪,就去医院周围给妈妈买一些好吃的。记得妈妈最爱吃糖葫芦,吃的香香甜甜的样子好像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大了,妈妈却老了,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手术后大概恢复了二十天时间,又做了一个月放疗。那是这么多年妈妈第一次没有在银川过年,在北京我的家中渡过春节,而爸爸赶回老家陪伴年迈的奶奶。妈妈给我包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现在我还能想起那饺子的香味,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妈妈包的饺子了。
妈妈拖着重病的身体帮我收拾年货、烙馅饼,好像大病初愈一般。放疗后妈妈身上的疼痛和不适暂时没有了,回到了老家。她甚至恢复了游泳,那时候的我天真的认为一切都在好转,癌症已经差不多被打败了。
三月份是每年爸爸妈妈例行体检的日子。结果出来了。爸爸偷偷打来电话,哽咽着说,妈妈的癌细胞已经骨转移了,又是一次晴天霹雳。我绝望又无奈,只能无语问苍天。妈妈又重新回到北京治疗,但这一次我们选择向妈妈隐瞒了病情。
靶向药、中药、针灸、气功、食疗,我们尝试所有能找到的抗癌方法,除了化疗。妈妈血管很细,平时输液就反应很大,所以对医生化疗的建议,她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化疗的诸多弊端,所以同意了妈妈的选择。感觉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赌博,无数次站在交叉路口,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可是诸多方法依然不能抑制妈妈的疼痛。有一次妈妈联系了一位以前认识的疼痛科大夫针灸,我事先给大夫发了短信,告知他妈妈的情况,并告诉他不要说漏了。这位大夫看着妈妈,表情很复杂,但还是鼓励妈妈要笑,帮助我一起隐瞒了病情。一次早晨坐在饭桌前,妈妈喃喃的说:“我是不是骨转移了呢?这么疼......”我赶紧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可是妈妈疼痛在不断加剧,她向我描述说感觉像有电钻在钻她的骨头,她夜不能寐。更要命的是,因为一侧肾已经在手术中去掉,妈妈坚持认为吃止痛药副作用太大了,会伤害到她的另一侧肾,所以尽量忍着不吃或者减量。我们也默认妈妈的观点。妈妈一向非常坚强,但有一次疼的嚎啕大哭,伏在我的肩上说:“蕾蕾,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心如刀绞,陪着妈妈一起哭,真希望那疼是在我的身上。
去医院疼痛科就诊,医生拿出一张疼痛分级的表格问妈妈情况,妈妈毫不犹豫的选择十级,是疼痛的最高级别。记得当时医生建议用吗啡,但手续很繁琐,我们当时认为吗啡不是毒品吗,会不会成瘾呢,在顾虑中放弃了这个选择。
有一次我已经想开口告诉妈妈病情的实际情况,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如何说。要告诉妈妈病情已经很严重,可能时间不多了吗?当时并没有医生明确告诉我们妈妈的生存期,只是说妈妈的癌细胞恶性程度比较高。可是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如果告诉了妈妈会不会就失去希望了呢?那时候我每天纠结痛苦,做事情的时候经常做着做着就泪流满面,但又不能当着妈妈的面哭。
就这样熬到了五月份,银川的医院有一位医生向爸爸推荐细胞疗法,妈妈决定回去试一试。出门时妈妈已经快走到车上了,又返回来紧紧抱住我,亲吻我的脸颊,妈妈一向很含蓄,很少这样动情,她说:“乖女儿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一直照顾我。”那是妈妈这一生最后住在我的家里。
回去后刚开始治疗的一个月情况还是不错的,感觉妈妈疼痛减轻了很多,精神状况也好一些了。开始还医院家里两边跑,但到了六月初情况急转直下,妈妈连下楼的力气也没有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才了解,癌症末期病人身体状况会有一个断崖似的下跌,急转直下。这一住,就再也没有回来。
妈妈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了,脸上开始出现黄疸。妈妈偶尔照镜子,会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们跟妈妈说,有些炎症。炎症消了就可以回家了。我每天躲在卫生间哭泣,尽量不让妈妈看到。有一次妈妈看着我说:“蕾蕾,不要这样难过,炎症好了不是就好了吗?”其实后来回忆起来,妈妈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的情况,聪明如她,只是不想让我们难过,而选择假装不知道。
就这样在互相的隐瞒中来到了妈妈最后的时刻。
那天早晨,妈妈突然就没了血压。紧急呼叫了大夫,给妈妈打了升压药,血压又上来了。但是那一整天,妈妈不是在昏睡中,就是焦躁不安,她坚持要起来上卫生间,不得已又给她插了导尿管。
那天下午,我女儿和哥哥的儿子刚刚结束考试,赶回银川,他们走进病房时,妈妈看到女儿,艰难的微笑了一下,呼唤女儿的小名。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她还深深记得她带过的外孙女,以后每次提起这个场景,女儿都会流泪。
晚上看着妈妈烦躁的情绪,我们商量放弃了对妈妈的抢救。凌晨12点,妈妈平静的走了。没有电影小说里的挣扎,没有大口的呼气,异常平静安详。在被眼泪模糊的双眼中,我仍看到了妈妈无比美丽灿烂的笑容,让我觉得妈妈一定是去了那个没有病痛的乐土。
逝者已逝,把哀伤留给了活着的人。那段时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经常在床上打着滚的哭,原来一个人的离开是这样的让人撕心裂肺。没有经历过死亡,也没有做好准备的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送走的是这个世界我最挚爱的母亲。我给妈妈发微信,给她写日记,假装跟她打电话,觉得自己真的有点不正常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我开始接触公益,才慢慢走了出来。做公益打开了我封闭的内心,在妈妈在世的日子,我更多的时间放在事业和家庭上,而做公益让我的内心向陌生人敞开。我努力关注和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着力于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自己能给予社会的价值,我感受到原来的焦虑、抑郁慢慢被平和与快乐代替,我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方向。我一直认为,是妈妈用她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尤其是我遇到了安宁疗护。
开始我只是做一个临终病人的陪伴志愿者,慢慢我发现其实我还可以做更多。
安宁疗护服务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者老年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的离世,以及减轻家属心理哀伤的一种服务。
安宁疗护是对一个人的终极关怀,是对病人身心社灵的全人关怀,是对生命末期全程的关怀,是对病人及家属的全家关怀,也是一个需要社会方方面面角色参与的全队关怀。
它不只是一个专业学科,也是一种生命教育。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生命教育,尤其是死亡教育,当家人或自己面对死亡时,就会出现我所经历的,被巨大的悲伤淹没,手足无措。医生也一直是被教育如何治病救人,没有一个学科是教授如何让人好好的走。可是死亡是每个人从生下来就要面对的,无一例外,没有一件事情像死亡一样,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如果在得知妈妈患癌症时,我接触过安宁疗护,可能很多经历会被改写。
记得妈妈在手术后休养的那段时间曾经跟我说过,她这一生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录制一张唱片,还有写一本个人的传记。可是我与家人后来都疲于对治疗的各种应对,完全没想到这两件事情其实可能是对妈妈最重要的精神支撑,根本就没有努力去实现。即使妈妈病重无法自己写,我也可以在陪伴她近八个月的过程中把她的生平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这对于她和对于我们将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可是现在她那些精彩的人生过往只能尘封了。
在妈妈的止痛问题上,其实也是悔不当初,如果是现在的我,会知道帮助病人止痛是第一要务,不会看着妈妈痛的死去活来,还在担心对肾的副作用。每每想起这些,仍心如刀绞。其实这是因为我从未接受妈妈要离世的现实。我一直在和死亡斗争、斗争,直到妈妈去世前两天,我还认为会有奇迹发生,而选择不相信医生的生存期预计。
另外一件最不应该的事情,是不应该向妈妈隐瞒病情。直到医生告诉我们可能只有一两周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勇气和妈妈说出实情,使得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别。甚至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问问妈妈,想在哪里离世。
学习了安宁疗护,知道了临终时需要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对大家是一个多么好的慰藉。爸爸那天说,因为没有和妈妈正式的道别,他一直心里很难过,六年多过去了,提起时他依然老泪纵横。
但其实在临终前的一两天,妈妈一直跟我说:“蕾蕾,我很幸福”。她其实什么都知道,她一直在暗示我,可惜当时我并未领会。
所以我欠妈妈一个四道人生,我想告诉妈妈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我要郑重的谢谢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把我养育成一个还算善良的人,我很惭愧,十八岁上大学离家后就很少陪伴照顾她,最后生病的这八个月虽然大部分时间陪在身边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我想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告别,暂时的分离,将来我们仍会在那个乐土团聚。
安宁疗护现在还不广为人知,这也是我和我的团队努力的方向。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可以这样对待死亡,原来在活着时越早了解就越能活的从容,原来临终时可以选择让自己和家人都更舒适一些、更有尊严一些。在众多癌末患者的身上,我能看到妈妈的身影,在众多无助的家属身上,我也能看到我的身影。如果能帮助更多人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帮助更多家属好好告别,做到生死两相安,更多的家庭能得到安慰,这个社会也就更和谐了。这是我迄今为止想到的我能回报妈妈,回报世界的最好方式。
这个方向是妈妈引领我来的,我将为之努力,为之奋斗。那天看到音乐人赵英俊的临终遗言,“希望你们别那么快的将我遗忘,只要还有人记得我,记得我的歌声,我可能就还在某个角落,陪伴着你们。我从小就喜欢下雨,若某个傍晚暴雨狂风,便是我来看你”,我想说,妈妈从未离开,喜悦时我会跟妈妈分享,遇到困难时想起妈妈便会坚强,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妈妈的血。在很多个瞬间,我都能感受到妈妈,和我同在,和荣基金的安宁疗护项目同在。
谢谢你,妈妈!仅以此文献给妈妈,致敬每一个为安宁奋斗的人,致敬所有信任和帮助我们的人!
作者/任蕾 | 2021年2月5日
(修订于202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