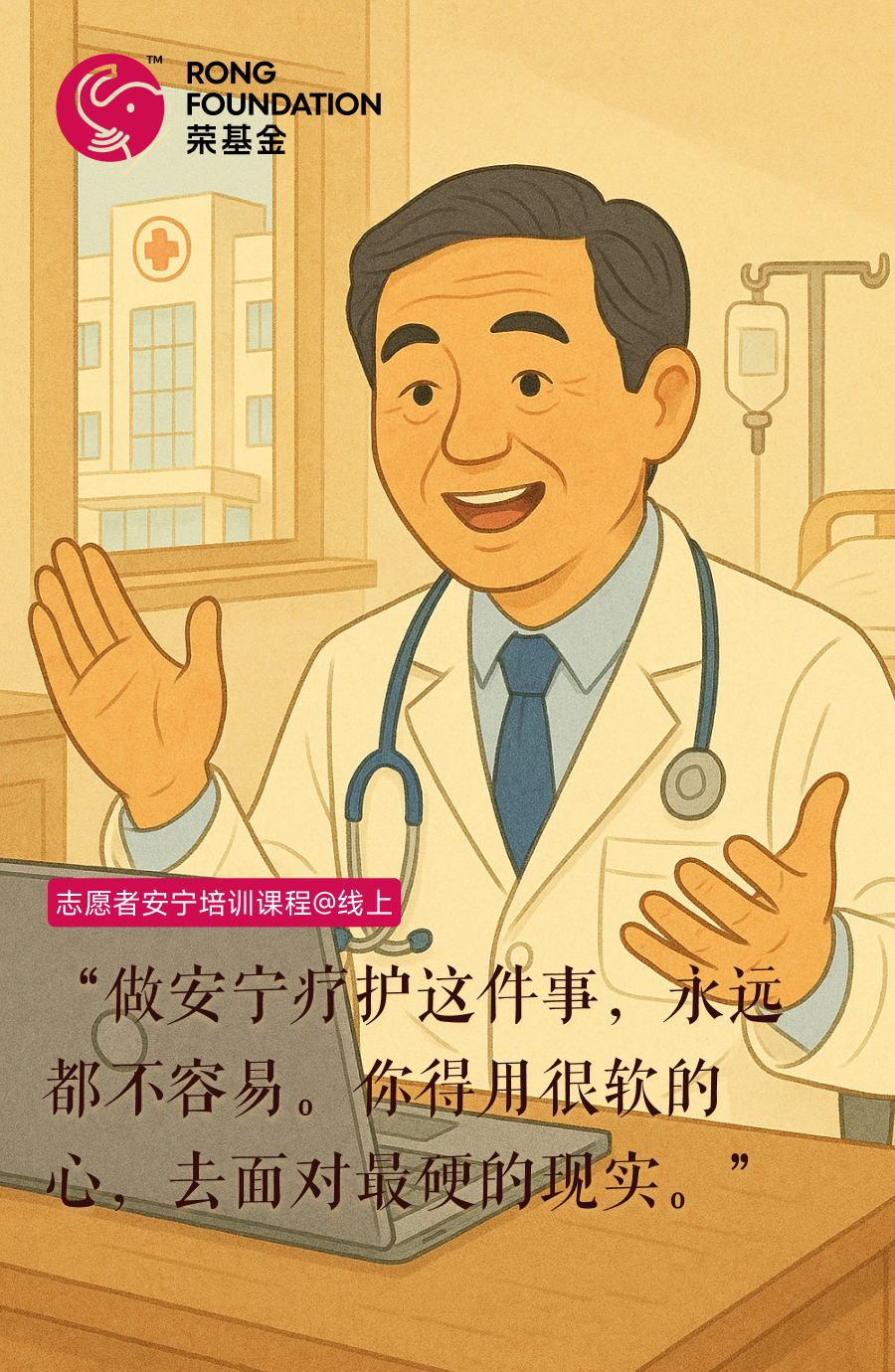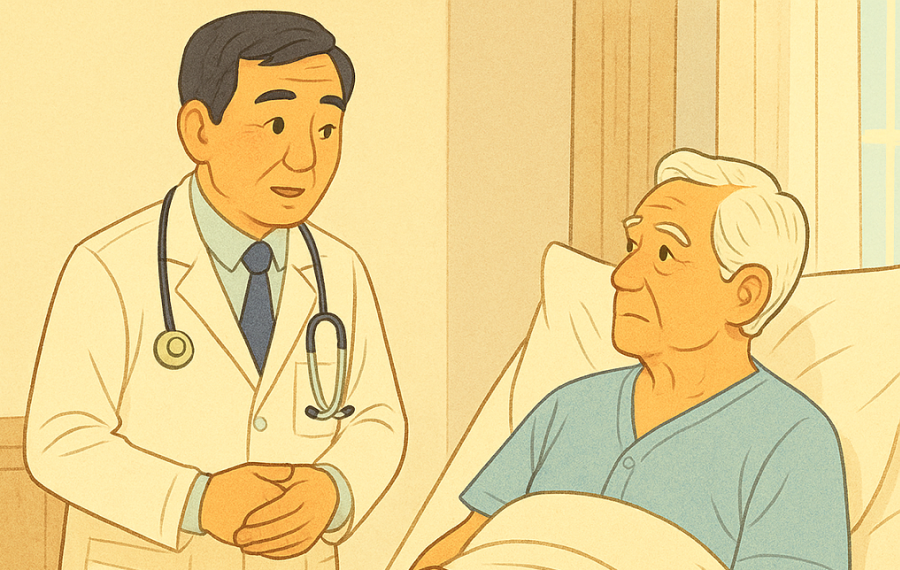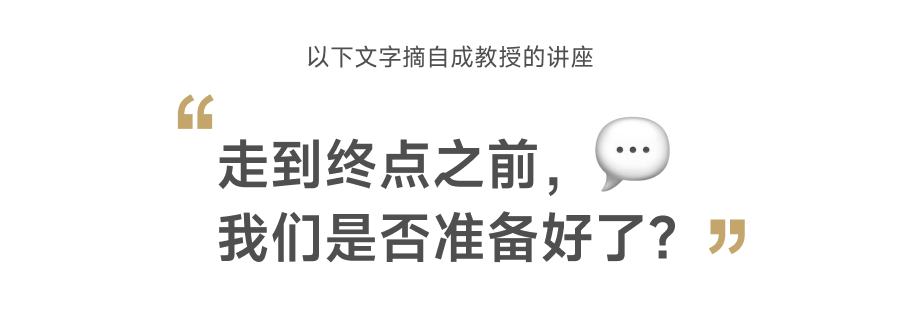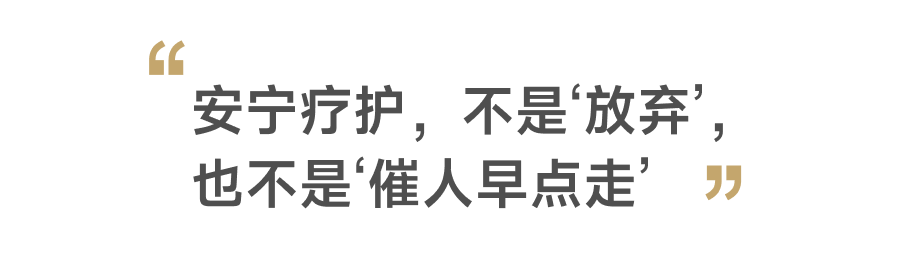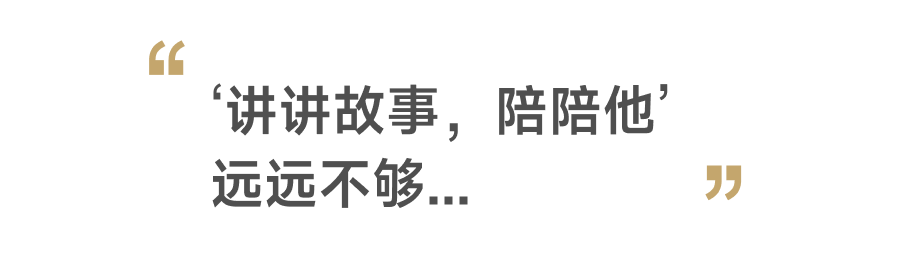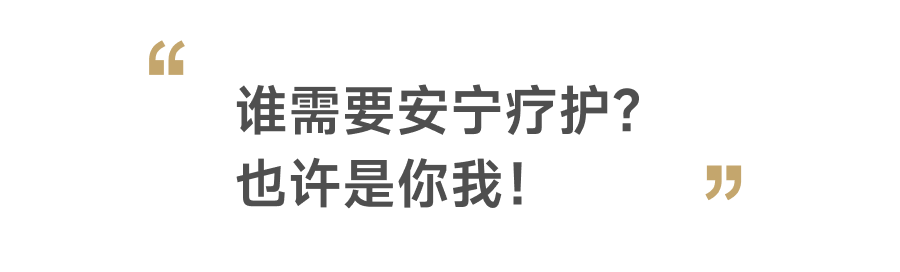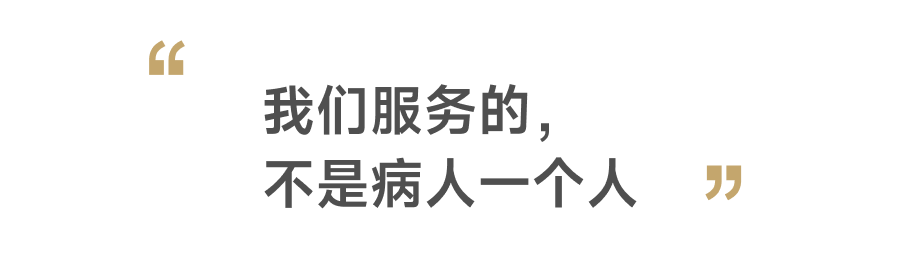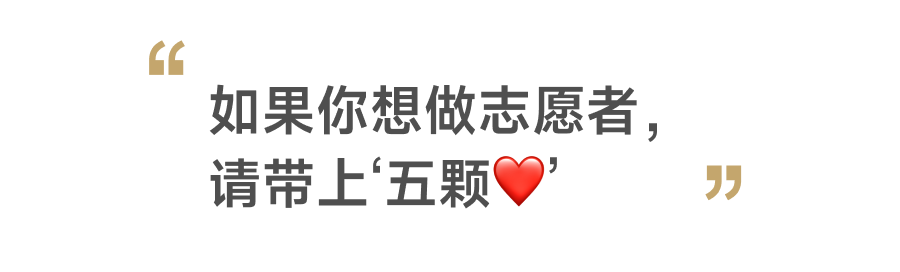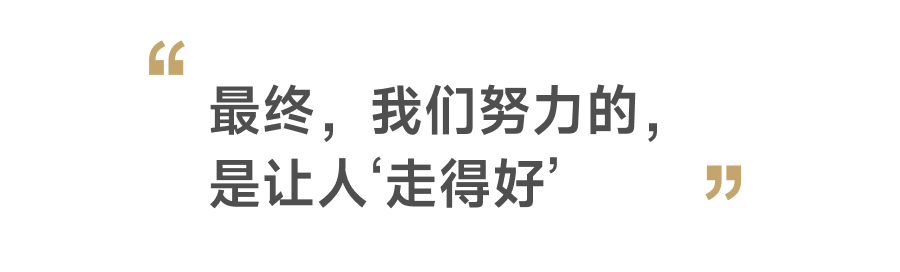那天晚上,屏幕那头的成文武教授,几次因为网络卡顿,画面倒着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笑着说:“证明我们的人生还是可以转弯的嘛。”那一刻,所有的志愿者伙伴都笑了。
或许,这正好是“安宁疗护”的诠释:即便终点注定,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温柔地转个弯,缓缓走完最后一程。
这是一场由荣基金组织的安宁疗护培训,成文武教授用一个多小时,带我们从根本上重新理解了安宁疗护。作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我国安宁疗护领域的专家,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满怀温情的老朋友,循循善诱地说起了“到底什么是安宁疗护”。
人这一生,总要学会面对一些事:分别、失控、痛苦,甚至死亡。
我做医生三十多年,做的是肿瘤科,尤其是那些“回天乏术”的病人。值一个夜班,送走三四个病人是常事。时间一长,我开始问自己:我们所谓“治不好了”的人,就只能忍着痛,等着走吗?
后来,我找到了答案:不是治不好,而是需要换一种方式照顾。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谈的“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而是调整目标。
当医生、病人和家属都清楚——疾病已经不能逆转时,我们就把重点从“延长生命”转向“提高生命质量”。
我们不加快死亡,也不刻意延缓死亡。我们尊重死亡作为自然过程的节奏,只是努力让它不那么痛、不那么孤单、不那么难堪。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边嚎啕大哭,一边要求医生“什么都做,管子插上、机器上着、再抢救”。也见过有人说,“医生,你就让他安乐一点早点走”。
但我们不能这样。医学不是替代自然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陪着走”,而不是“决定怎么走”。
我时常提醒一些初入这一行的朋友:别以为安宁疗护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安宁疗护的工作有两个核心支柱:
第一支柱是:症状控制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病人的痛苦。不是“控制一下”,而是精准、有系统地减轻那些具体而巨大的痛苦:
如果这些没处理好,你跟病人说再多好听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我们说“让病人舒服”,这个“舒服”是非常具体的身体层面的任务。
第二支柱是:支持治疗
-
营养支持:吃得下、吃得够,是活下去的基本保障;
-
心理支持:要能让他安心、释怀、不孤单;
-
社会支持:有些问题是家庭冲突、财产纠纷、养老难题,甚至葬礼费用,这些都需要“社会系统”出手,包括志愿者、社工、法律、宗教、邻里、保险等等。
我常说:我们不是来锦上添花的,我们是来雪中送炭的。
有一次,我问培训班上的志愿者:“你们觉得,安宁疗护服务谁?”
大部分人回答:“晚期癌症病人。”
这答案对,但远远不够。
不是只有肿瘤病人需要安宁疗护。
渐冻症、老年痴呆、脑卒中、植物人、感染终末期、重症儿童,甚至地震灾难后失去亲人的家属……他们都需要。
说得更直白一些:每个人都需要安宁疗护!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会不会是倒下的那一个。哪怕今天健康,明天可能一场车祸、一次出血、一个意外,就把我们推向终点。
安宁疗护不仅仅是照顾“将死之人”,它是一种提醒:我们该怎样活,该怎样走。
在安宁疗护里,我们永远不是只面对“一个病人”。
我们照顾的,是一个照护单元。这个人,以及围绕他的所有亲人、伴侣、孩子、朋友。
有人临终前最大的牵挂不是自己,而是女儿高考、老伴没人照顾、孙子不认得他。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放下这些牵挂,让他能安心地、体面地告别。
哪怕他已经沉睡,能不能为他放他喜欢的音乐、放几张家人的照片?这些,都是安宁疗护里“最小的温柔”
我一直和志愿者说,安宁疗护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事。你必须准备好,带着“五颗心”:
-
爱心:有爱,才会愿意靠近痛苦的人;
-
耐心:面对不理解你的家属、不回应你的病人,你不能退缩;
-
恒心:不要三天热度。一段稳定、持续的陪伴,是最大的安慰;
-
细心:一句没说对的话,会刺痛一个本就脆弱的家庭;
-
勇敢的心:你会看到很多离别,要面对很多“救不了”的结局。你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被这些情绪拖垮。
我真的见过志愿者因为某个病人的离世而抑郁、焦虑,自责到几乎崩溃。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组织能提供“心理督导”,守护这些有爱的人。
我年轻时做的是晚期肝癌的治疗,“几乎见一个死一个”。
所以我曾问我的老师,这个病有没有‘金标准’的治疗?老师说:如果你能让一个患者,在有限的生命里,过得没有痛苦、有尊严,那也是一种金标准。
得知我要去美国进修安宁疗护,一个领导开玩笑说:“小成,你去学本事回来,要是你床上的病人死了,家属都不哭,我们就服你。”
那时候我觉得他在扯,哪有人死了家属不哭的。
可真的有。
我在美国见到的病房,病人走的时候,家属围着他唱歌,读诗,牵手,亲吻,说再见。不是他们不爱,而是他们已经陪完、道别完、安慰完、接受完了。哭,不再是唯一的出口。
我回来后,照着他们的理念做。后来我们有病人走了,家属对我说:“成医生,我们不哭。你已经帮我们把最难的这段路走得很好了。”
那一刻,我觉得我没白学,也没白走这条路。
当讲座接近尾声,教授说:做安宁疗护这件事,永远都不容易。你得跨过医学、心理、伦理、沟通、文化、制度这些关卡。你还得用很软的心,去面对最硬的现实。
但如果我,还有你们,都能为这件事多做一点点,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变得不一样。
我常说:“我们不是在和死亡战斗,而是在和无意义、和遗憾战斗。”
让每一个生命,有始有终、有爱有告别、有尊严有意义。
这,才是安宁的真正含义。